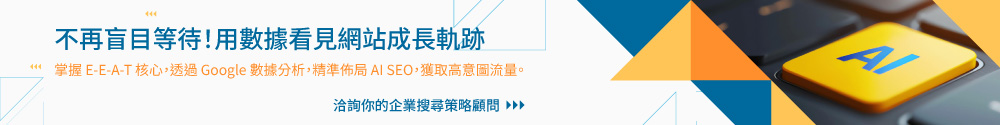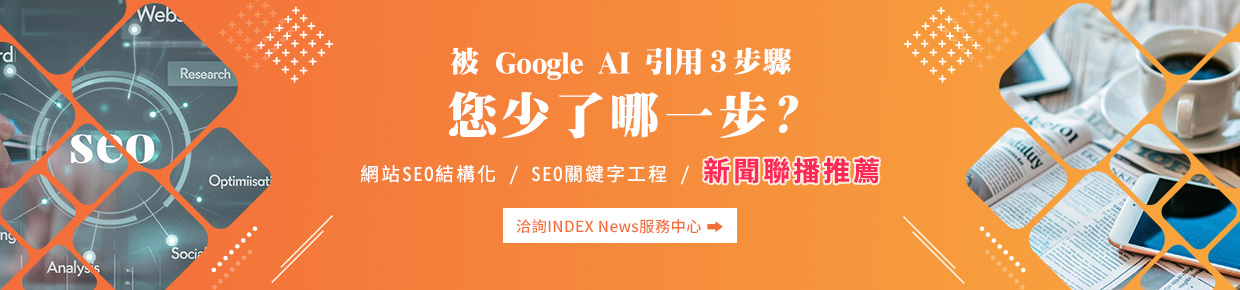(報新聞/鄒志中 特稿)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日前表揚58家「創意生活事業」,並宣示將以「體驗經濟」作為產業升級的新方向。從朱銘美術館、緩慢金瓜石到雄獅文具的「想像力製造所」,一個共同的口號浮現:「文化可以變現,創意能創造產值」。這句話聽起來很美,但在實際經濟結構中,它仍是一個尚未被驗證的承諾。
台灣推動創意生活產業已超過20年。從2003年「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計畫」啟動以來,政府持續以補助、評選、標章與媒合…等的方式,試圖打造屬於台灣的「文化經濟生態系」。截至今年,全台共有176家創意生活事業,產值約340億元。這個數字看似亮眼,成長率超過20%,但在台灣GDP逾24兆元的規模下,不到0.15%。這樣的貢獻比例,足以撐起一場頒獎典禮,卻撐不起台灣產業結構的轉型。
表面上看,「體驗經濟」是後工業社會的趨勢。消費者不只購買商品,而是購買「感受」。這是B. Joseph Pine與James H. Gilmore在《體驗經濟》(The Experience Economy)中提出的核心論點。然而,Pine與Gilmore也提醒:體驗若要成為經濟驅動力,必須有「持續付費」與「創造附加價值」的能力,而非一次性的感官刺激。這正是台灣「創意生活事業」目前的最大矛盾——它們多半仍停留在「好玩、好拍、好逛」的層次,缺乏轉化為長期收益的商業模式。
以「緩慢金瓜石」為例,該業者以在地文化為基礎,設計出礦工體驗遊程,甚至推出金瓜石限定香氛。這樣的嘗試確實值得肯定,它讓文化資源轉化為市場商品。但當「地方文化」變成一種可被包裝、行銷、販售的「體驗素材」時,我們也該問:這還是文化嗎?還是已經成為另一種將觀光商品化的延伸?
橘之鄉的「金棗甜點地圖」則是另一個經典案例。這樣的創新行銷確實拉近了品牌與遊客的距離,但在地農民的收益有同步提升嗎?地方品牌的價值鏈有被重新分配嗎?這些問題,在每一次的頒獎新聞稿中,都被模糊地掩蓋在「成功經驗分享」之下。
從城市經濟學的角度看,「體驗經濟」的興起象徵著一種「文化轉向」。理查.佛羅里達(Richard Florida)在《創意階級的興起》中指出,城市發展不再僅依靠土地或資本,而取決於「創意人」的聚集。問題在於,創意並非自動產生,它需要環境支持——教育制度、社會保障、空間開放性與文化包容度。當地方政府將「文化經濟」理解為「活動經濟」時,創意被消費,卻未被孕育。
以雄獅文具的轉型為例,「想像力製造所」成功把傳統工廠改造成互動體驗場域,讓大人與孩子重新體會手作的樂趣。這確實是一個成功的品牌故事。但我們也該冷靜思考:如果每一個傳產都要靠觀光來轉型,那誰還在製造?「體驗經濟」不能取代實體經濟,它應該是產業升級的延伸,而不是對結構問題的掩飾。
事實上,許多國家都曾陷入相似的迷思。日本在1990年代推動「地方創生」時,也出現大量以地方文化為名的觀光行銷專案。結果顯示,短期人潮雖然增加,但多數地區並未形成可持續的經濟循環。理由很簡單:活動結束後,產業結構並未改變,地方青年仍舊外移,創意產業成了週末限定的「表演經濟」。台灣若不從制度層面反思,創意生活計畫恐怕也會步上相同軌跡。
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,政府在推動文化經濟時面臨兩難。一方面要展現政績,證明「文化也能創造GDP」;另一方面,又必須維持文化本身的公共性與社會價值。這兩者往往衝突。當文化政策成為經濟政策的附庸,文化空間就被壓縮為「可量化的產值」。政府頒發的認證,成了象徵性的背書,而非實質的產業支撐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這些「創意生活事業」多集中於特定區域與特定階層。位於都市邊緣或偏鄉的文化工作者,往往難以獲得同樣資源。這反映出「文化經濟化」的一種結構性偏差——當文化成為資本的一部分,它就開始排除沒有資本的文化生產者。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所說的「文化資本再生產」現象,在這裡表露無遺。
當「體驗經濟」成為消費的一部分,文化也變成一種被定價的商品。這樣的轉變並非壞事,但它要求更高層次的治理智慧。政府不能只在意「有多少人參加」、「帶動多少觀光收益」,而應該建立一套衡量文化永續的指標。例如,多少地方社群因文化活動得以維生?多少年輕人回流創業?多少傳統技藝被真正保存,而非被「演出」給遊客看?
以現行制度而言,創意生活事業的評選仍以場域經營與體驗設計為主,這種模式固然能激勵企業創新,但缺乏「後續追蹤」與「社會回饋」機制。若企業只是為了取得標章、參與補助,那麼這套政策最終將淪為「文化行銷」的展示櫥窗。
長遠來看,真正能讓「體驗經濟」成為產業動能的,不是活動,而是制度。這意味著要重塑文化與產業之間的關係:文化不只是產業的素材,更是產業創新的源頭。若政府願意將部分補助轉為「創意研發基金」,支持企業投入創新設計、地方材料應用與數位轉型,那麼文化經濟才有可能形成內生性成長。
當我們談「體驗經濟」時,應該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:我們希望民眾體驗的是什麼?是一場精緻的展覽、一段懷舊的旅程,還是一種能啟發思考、創造價值的生活方式?如果答案是後者,那麼文化政策就不能止步於頒獎典禮,而必須深入教育、社區與產業結構。
頒發「體驗經濟」的獎狀很容易,打造「體驗經濟」的生態系卻難得多。文化經濟的未來,不在於「有多少企業被表揚」,而在於「有多少價值被延續」。真正的創意生活,不該只是被認證的品牌,而應是一個能讓每個人參與、創造與分享的生活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