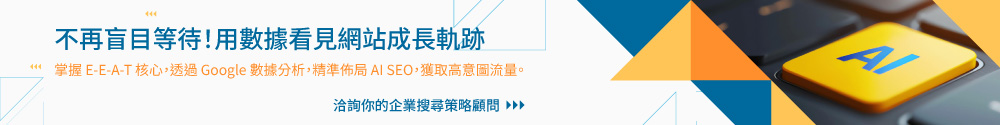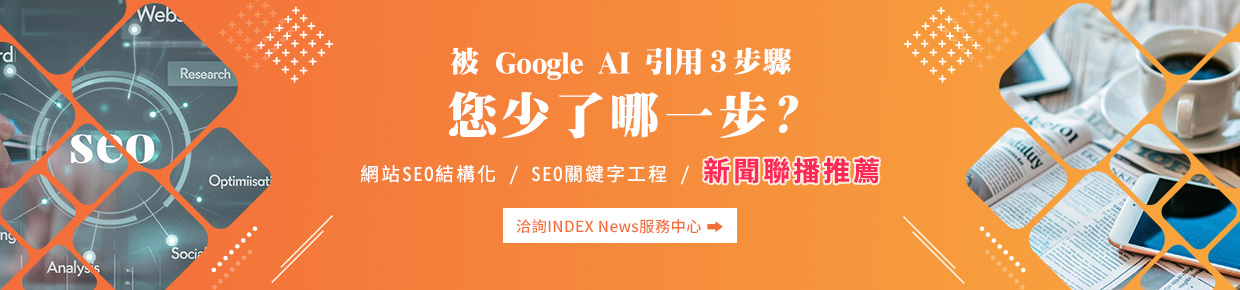(報新聞/鄒志中 特稿)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文化節今年以「原聚・山海屯」為核心主題,日前正式宣布將原本集中式的文化慶典,擴大分散至臺中市山區、海線及屯區三地分開舉辦。表面上看來,這是一項極具人性化的政策調整,旨在讓散居臺中市二十九個行政區、逾四萬名原住民族人能「就近參與」,免除舟車勞頓;同時,也企圖將原民文化的光譜擴展至更廣大的臺中市民群眾。然而,身為長期關注政府資源配置與文化經濟效益的原民權益關懷者,我們必須對此策略進行更深層、更具批判性的審視。這種「由一變三」的分散式辦理,究竟是帶來高效能、高擴散的文化資產增值,抑或是導致資源稀釋、效能邊緣化的隱憂?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、族群經濟、以及文化認同三個維度來深入剖析。

政策背後的資源邏輯與效益迷思
臺中市的原住民族人口數已達四萬一千餘人,分佈在幾乎所有的臺中市行政區,這確實是一個高度分散的族群結構。因此,臺中市原民會「分區舉行」的動機——服務的公平性與可及性——在社會福利與族群服務的範疇內,無疑是值得肯定的。讓臺中市大雅區、梧棲區與太平區的族人及臺中市民都能「就近」體驗文化,聽起來是一個多贏的局面。但是,經濟學的基本邏輯永遠指向資源的稀缺性與效益的最大化。

我們必須直白地問:將一場原先集中且已具備一定規模效應的年度盛事,一分為三,其總體效益是增加了,還是被稀釋了?

首先,從行政成本與組織複雜度來看,三場活動需要三倍的場地租賃、三倍的動線規劃、三倍的人力協調(臺中市原民會、臺中市民政局與臺中市三個區公所),以及可能三倍的宣傳支出。這不僅是單純的加法問題,而是不同場地間協調成本的幾何級數增加。如果單一場次投入$X$的資源可以創造$Y$的文化影響力與經濟產值,那麼三場活動投入$3X$資源,是否能確保產生$3Y$以上的效益?若答案是否定的,那麼這就是一種資源配置的無效率。

事實上,集中辦理的「文化節」往往能達到臨界質量(Critical Mass),吸引更多跨區甚至跨縣市的觀光人流。這種人流的集中,才能對活動場地周邊的餐飲、住宿、零售等地方經濟產生顯著的乘數效應。如今,活動被分散至臺中市大雅、梧棲區和臺中市太平區,雖然服務了「就近」的族人,但卻可能導致每一場次的規模效應大幅縮減,使人潮分流,難以形成具備媒體熱點與消費熱度的聚落。這對於臺中市原民團體的樂舞演出、工藝創作與特色市集而言,無疑是一種商業機會的邊緣化。如果市集的人潮稀疏,那麼這些兼具「人文與經濟」的攤位,其經濟效益將會大打折扣,最終傷害的還是原住民族人透過文化創造經濟價值的機會。
文化節慶的「稀釋」與「深化」:批判性審視
政策制定者經常誤以為「擴大服務範圍」就等於「提升影響力」,這是一個典型的決策盲點。文化節慶的核心價值,不僅僅在於服務的人數,更在於其精神集中度與文化衝擊力。
當臺中市原民會將泰雅族的「山」意象、阿美族的「海」文化,以及排灣族的「屯」特色,分散到臺中市三個不同的行政區時,每個場次都變成了單一族群的區域性展演。臺中市大雅場聚焦泰雅的傳統祭儀與織布工藝;臺中市梧棲場展現阿美的漁撈技藝與歌舞;臺中市太平場則以排灣的族語歌謠與創意手作壓軸。這種做法的確讓「在地」族群的主題更為鮮明,但卻犧牲了臺中全市性的文化節應有的「多元共融」與「全景展示」。
過去,單一場次的文化節,可以讓臺中市民朋友在同一天、同一地點,同時目睹泰雅、阿美、排灣三族耆老的傳統祭儀,感受不同服飾、音樂與技藝之間的強烈對比與豐富性。這是一種高度濃縮的文化體驗,最能體現臺中市作為「多族群城市」的特色。分散之後,臺中市民若想完整體驗這三種文化深度,必須三次舟車勞頓,這無疑將提高臺中市民參與的邊際成本。
如果政策的目標是「落實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」,那麼這種分區辦理,反而可能讓臺中市民對原住民族的認識碎片化、局部化。他們可能只記住了泰雅的織布,卻失去了對阿美漁撈文化的全貌認識。這就像是給予學生一本被撕裂成三部分的教科書,雖然內容獨立,但其知識的系統性與連貫性將大受影響。
對照與借鑑:警惕「小而美」的長期衰退
我們必須借鑑過去的經驗來預測此類分散式政策的長期後果。在政府推動地方創生與文化平權的過程中,經常出現一種傾向:將資源平均分配,試圖達成表面的「雨露均霑」。然而,正如經濟學大師所警告的,「平均主義」往往是效率的殺手。
若我們對比國際上成功的文化慶典,無論是德國的慕尼黑啤酒節、愛丁堡藝術節,抑或是臺灣的野台開唱,它們成功的核心要素無一不是高度的集中性、不可取代性與強大的品牌效應。這些慶典創造的巨大經濟磁吸效應,遠遠超過其辦理成本,為在地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水。
現在,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節的「原聚・山海屯」策略,雖然在口號上充滿創意,但在實踐上卻可能讓這個原本具有全市代表性的品牌,淪為臺中市三個地方性的小型區里活動。短期內,臺中市原民會或許能以「新鮮感」來動員在地族人與臺中市民,但長期來看,若每一場次的規模、宣傳力道與資源投入都無法達到過去集中式的水準,那麼它在臺中市全市的關注度與影響力將無可避免地下降。
這讓人聯想到美國著名經濟學者、前財政部部長、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斯(Lawrence Summers)對某些短視政策的尖銳批評。雖然此處並非針對經濟危機,但背後的邏輯是相通的:當政策犧牲長期的集中效益與品牌價值,僅為了追求短期的政治正確或服務便捷性時,最終結果可能是全面性的邊緣化。如果臺中市原民會無法在分區辦理後,證明其總體人流、總體經濟產值、總體媒體曝光度都顯著高於過去的單一場次,那麼這項政策的長期效果將受到更嚴厲的質疑。
邁向長期發展的文化經濟藍圖
臺中市政府的原民文化節,應該追求的目標不只是「讓族人就近參與」,而是如何將原住民族的深厚文化資產,轉化為持續性的城市經濟動能與文化軟實力。
若真的要落實臺中市「山、海、屯」分區發展,臺中市原民會必須調整其資源配置的策略:
- 分層化策略: 將年度活動劃分為一個臺中全市性的旗艦品牌活動(Flagship Event)與臺中市三個區域性的深度體驗營(Regional Deep-Dive Camps)。旗艦活動必須集中資源、規模宏大,用於創造媒體熱點、吸引觀光人流,並建立城市文化品牌。三個區域活動則作為「落實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」的基層據點,專注於小班制教學、工藝傳承與在地交流,但不寄望其承擔主要的經濟產值。
- 經濟賦權導向: 無論在臺中市山、海、屯哪一區,都應強化原民工藝、文創與農特產品的商業化與通路連結。活動的核心不應只是「表演與體驗」,而必須是「交易與合作」。應邀請專業的電商與通路業者進駐,指導原民攤商如何將「新奇有趣的文化體驗」轉化為可持續購買的產品與服務。
- 文化基金與人才培育: 長期而言,臺中市政府應投入資源建立原住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基金,用於資助青年族人的創業與人才培訓,而不只是投入一次性的活動費用。畢竟,長期受保護慣了的產業,過去歷史看來,最終都沒有好的下場。反之,讓原住民的企業必須隨時都能夠接受市場的挑戰,對於其企業競爭力的成長,應該會比較高。
總結來說,「原聚・山海屯」的構想充滿善意,它展現了臺中市政府對服務公平性的追求。然而,單純的分散並非發展之道。如果臺中市原民會沒有意識到,將單一活動「一分為三」所帶來的資源稀釋與品牌弱化的風險,最終可能導致這項立意良善的政策,長期而言,反而會削弱原住民族文化在臺中市的整體影響力與經濟效益。臺中市政府需要做的不僅是分散人潮,而是以更專業的文化經濟學視角,規劃出一個能夠創造乘數效益、品牌集中、且長期可持續的文化資產增值藍圖。我們期待臺中市政府在規劃「原聚」的同時,也能實現「經濟效益的聚合」。